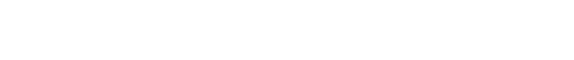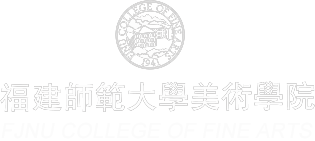缪鹏飞
(美术学院1954级校友,澳门理工学院艺术高等学校教授)
怀着兴奋、忐忑的心情,第一次跨进师大大门,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了。当时我二十岁,还从未单独离开过家乡。那时的交通非常不便,鹰厦铁路尚未建成,好像是到三明,再转乘汽车,奔波了二天才抵达的。福州给我的印象,首先是街道上成排倾斜的灰色木屋,我诧异于很多人活动期间它并没有倒下。套上黑色眼罩的马车,叮叮当当的在街上行走,也很令我新奇。温泉路上有很多浴室,二片装有弹簧的小门闪动,男女共处一室休息,风气很开放。经过了天桥,行到仓前山,有一群西式建筑和教堂,那就是艺术系的所在地,风景不错。五十年代的福州是前线,台湾海峡的形势很紧张,时时听到连番的炮声和飞机的轰鸣声,起先学生老老实实的躲到防空洞里,后来习惯了,午睡时间听到警报也不起床,不当一回事。
当时最大的梦想是到苏联去,满脑子的幻想,满脑子的梦。耳边时时响着低沉的伏尔加船夫曲的旋律,眼前出现列宾的“纤夫”、赛洛夫的“桃子与少女”,还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梦着无边无际雪地上的三套马车,发奇思于天外。梦,做完一个又一个。
南方阳光充足,绿荫满地,树上蝉鸣不停,令人慵懒得不想起床,有时午睡到三点钟还不起来,国画老师林子白先生到宿舍来找我们,我们请他画只公鸡给我们看看,或者一时兴起,躲进石膏像室,不让老师发现。
班主任陈运义老师瘦削、微秃、英俊,拿着根烟斗,不停地吐出一圈圈的烟,好像契诃夫小说“带阁楼的房子”里的画家。他腼腆、羞怯,不善辞令,讲话很少。在我们那个年龄,体会不到中年人得感情,似乎他有所企盼,有些隐痛,毕业后我曾遇到过他一次,在上海,我曾请他看我的画,期望他指出一点方向,他只鼓励我从政治上多学习、多上进,对画没有提一个字的意见。我想这大概就是那个“言不由衷”时代的特征吧。
谢投八主任不大和我谈政治,可学问、艺术,渊博深邃,学校里我最敬重他。他一瘸一拐地到教室里巡视,帮我们看画的形象,常常萦绕在心头。记得毕业时,我模仿雷诺阿的风格画了一些“节日的灯饰”,现在想起来那张画素描关系很松,当时我沉醉于华丽的色彩效果。谢老师看了良久,对我说“要老老实实地画,不要搞花样”,当时我不以为然,一团兴奋顿时消失。但这次诲导,却深深印在我的心上。年轻时心态浮躁,喜欢追求表面效果,事隔多年,我自己的心态沉了下来,才体会到其中的真意和苦心。
学校生活理应是人们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日子,可那时是一个多事之秋。到学校半年多,运动就开始了,除四害、大跃进、反右,一些老师成了右派,连学生中也揪出了右派,认真学习的同学反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批判的对象,画画成为偷偷摸摸的勾当。离开学校后的道路更艰难了。这才明白艺术可能要你付出一辈子的心力。可能你一辈子穷,一辈子都辛苦,一辈子都没有回报。在荷兰, 我特地去了伦勃朗在阿姆斯特丹的那间曾带给他辉煌岁月的大屋,坐在那里,想到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将面临破产,离开大屋后再也不能回来,不禁悲从中来。他原本可以舒舒服服地生活的,但为了艺术的真诚,社会遗弃了他。可悲地离开人世。这是何等的不公平,老天爷对真正的艺术家常常不公平,可艺术家的梦也总是不醒。至今我的梦还没有醒,它曾经支持了我度过几十年的艰难岁月,或许还将继续支持着我度过余生。至今我不能应对周围的世界,不能,也不会在市场、画廊之间周旋。与我同时代的艺术家有很多人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为了圆一个梦,而付出了一切,一身在坎坷、贫困中度过。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
我多羡慕新一代的年轻艺术家,他们学习的条件好得多,道路也宽广得多,机会也多得多,也许他们也在做着不同的梦,愿这些梦能支持他们一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