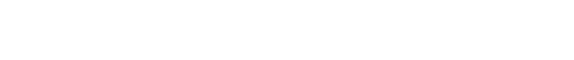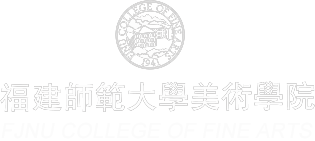王福阳
(美术学院1976级校友,福建儿童发展职业学院副院长、教授)
写下追梦的记忆,因为没有断,爱才连着情。
76级,最后的“工农兵学员”
说最后,是因为76级与77级入学时间仅隔半年,准确地说76级是1977年3月份录取入学的。此前一年,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去世,唐山大地震,毛主席去世,粉碎“四人帮”。 我们记住那是中国历的龙年,却是天灾与人祸交错的一年,我们这些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插队知青终日在激奋与不安中度日。村头的大广播、大队部的报纸和二极管收音机成了我们的至爱,报纸通栏标题非常大,一会儿红,一会儿黑,大家开始在迷茫混沌中找寻出路:有人因病返城,有人开后门招工返城,极少数找个小芳就地幸福了。对我来说,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上大学,上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
艺术系76级美术专业45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有5位来自部队,还有工人、教师,大部分是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知识农民,没有应届生,年龄相差七八岁左右,如此杂混的组合很容易让时下人感觉工农兵学员文化低、专业差。其实,至今我还是觉着用“专业文化良莠不齐,实践能力时代造就”来评价更好。作为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批大学生,我们也经过了文化考试和专业面试,文化考试统一安排在县一中闭卷进行,专业面试是由师大艺术系派出的林碧锋老师在县文化馆组织的,素描写生是“赤脚医生的药箱和雨伞”,创作考试命题是“欢庆粉碎 ‘ 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这些小试对已经画过不少巨幅领袖油画和宣传画的我不算什么,我们绝大部分同学也都在农村或社会上小有成就,当然也有个别同学是当地推荐的,从零开始探求艺术。刚入学时,南平来的徐新生同学原本就是中学的美术教师,他拿出之前临摹的格里高莱斯库的作品,让我们十分吃惊和羡慕。德化瓷厂来的颜德开描画的瓷瓶仕女那是一个了得,更让我这个自认为参加过全省美展、出版过小连环画的高手,连续两个暑期假借护校拼命恶补文化和专业。
76级的同学懂得“面朝黄土背朝天”和“只争朝夕”的真正含意,学习氛围和兴致就两个字——“自觉”。老师们也大多是刚刚从下放农村返校的,他们住在教学楼的地下室和简易平房里,高一呼老师的靠厨房的围墙被小偷打了个大洞,倒为我们抓贼提供了方便。杨启舆老师的地下室离我们班种辣椒的菜地很近,他画的小品我们每人都有几张,那是我们用菜地辣椒换来的,福州人不吃辣,但对湖南籍的杨老师而言那可是宝贝啊。那时我们与老师少有陌生,有的是专业崇敬,师生对艺术及思潮的讨论、对专业的探求学习,是融合在一种没有隔阂的情态中完成的。
今天,我们自豪地向母校汇报,艺术系76级美术专业45位同学中有现任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博士、珠海大学设计学院副院长陈方远教授、闽江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刘君博教授、福建儿童发展职业学院副院长王福阳教授、福建省画院副院长孙志纯、国家一级美术师刘秉贤、上海文艺出版社资深美术主编王志伟等著名画家、教育家10余人,还有长期服务于全省各中学、高校的美术教学一线骨干教师、校长20余人,以及担任上海市卢湾区商业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的谷峰等企业家、漳浦县文联主席林仲文等文化教育部门县处级党政干部10多人。
同学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泛彩,我无法一一记下他们的业绩,但我们都永远感恩我们成长起步的福建师大艺术系。
师大与大师——谢投八教授
入学前我的启蒙老师许金宝、沈长城就告诉我,福建师大艺术系的谢投八教授是徐悲鸿留法时的同班同学,哇,在想象中那就是神啊。1975年秋天,、作为知青业余画家第一次到省城参观美展,沈长城老师带着我专门拜访了谢教授,那时我躲在老师的背后不敢多出声,没想到一年后入学第一次面见他,他却说:“我认识你,长城的学生”。他个头紧小,不苟言笑,穿戴十分干净, 一字胡须,一头白发,双目可亲有神,因腿脚不便拄着根拐杖,老远就能听到他来的声响,人还未到,我们的任课专业老师就会要求大家迅速整理画室,搞好卫生,我们是既喜欢又害怕他。虽然他手中总燃着一根卷烟,但从来不将划过的火柴丢地上,而是将用过的另一头插回盒子里。他脚上的皮鞋永远是油亮的,现在细细品来却也是精致严谨的风度。
我们一组画室在传达室斜坡边上,与他所住的小洋楼相距不到50米,记得一年级时的一个晚上,我一人在画室,正聚精会神地细微刻划佛兰克里石膏头像,完全没注意到谢老已在我的身后站了许久,他告诉我:“这种长期的作业,只要体会式地画一、二张就可以了,你这样画我看不出你画的精神,被磨平了,磨腻了。”他要求我当着他的面每10分钟、5分钟画一张又一张的速写,也不知画到几点,地上已堆了一叠他提倡的快速的、三级明暗的习作。
他主张学生要解决好快速捕捉对象的状态能力与长期作业训练造型能力的关系。有一次,我们全班在画胜利女神石膏像的时候,他来到画室看了许久,提议大家停下来听他讲女神的故事。那天的课上得很放松,在听故事交谈过程中,谢老突然对女生范艾青说:“女同学画得非常好, 但一定要照顾好家庭和孩子,处理好家庭和孩子后画画才安心啊。”一席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女生脸涨通红,其实她们那时都还没有成家,真不知谢老的心思神游到何方,大家开心了一上午,至今难以忘怀。谢老极力提倡的捕捉造型新鲜感、强调线面结合的三级明暗调子造型的教学方法,与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苏联契斯恰柯夫素描教学体系是不同的,但那时的艺术系美术专业并没有完全以契斯恰可柯的体系为美术教学的唯一方法,而是倡导多元的认识和多样的教学方法,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研究与实践。
对谢老的回忆总在许多温情之中。一天傍晚,我和学习委员陈方远拿了一叠近期的画去他家请教。大客厅的百叶窗关得较暗,把画放好后他叫我走到门口去,让我背过身、低下头、弯下腰,从胯下看背后自己的画,好一阵后才让我说有什么发现。人的动作变了、视角变了,对象也变了,其实他就是要我破坏固定的、常规的形象感觉,自己评、自己找问题、自己解决问题,这样别出心裁的教诲终生难忘。至今,我仍然以这些方法和态度来改进我的教育教学。我们的每一次作业汇报、大小展览他都会到场观摩指导,毕业前夕,他亲自召集并主持我们班的座谈会,记得最牢的就是他要求我们的“四多”:即多画创作小构图,多画速写,多读书,多听音乐。当时,他虽然已退休不当系主任,但还是那样的关心人才培养和艺术系的建设发展。这就是大师的大气、大师的大爱、大师的风范。
从地下转到公开的“真理”大讨论
1978年5月初,连绵阴雨间隔着少见的晴日,闷热的天气杂揉着压低嗓门的争吵。“什么是真理?”“真理有标准吗?”“凡是毛主席说的都是真理吗?”没有“舵手”的中国要走向何方?这个直面当时中国社会最敏感的话题讨论,是在我们一周两个下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上进行的。
吴恒老师个头不高,短发梳得笔直发亮,江浙口音的高频音调总能控制好争执的对话,她不时地从藤编小篮中拿出些小册子和小纸片,一字一句地念着,其中有我们不能看的内部刊物。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场被规定离开教室就不能再说的悄悄讨论是在5月11 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前后展开的。这场大讨论,一开始就超出了理论讨论的范围,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无论是支持或反对的一方,都认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一场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说实话,我们当时并不十分清楚党内斗争问题的理论方向,但那次约半个月的讨论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师大知识分子们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敏锐把握和深切关注、所担负的使命,以及对国家、对民族振兴的思考和对学生的引领。同学们也私下交流,深感大学里的学习不仅仅只是专业技能上的追求,更领悟到什么是“匹夫有责”的国家使命感。我想,这就是大学教会我们的大思考。
小黄楼的广播站
师大四百米田径场西头那座欧式三层小黄楼,你一进校门穿过林荫大道就能看见它。四根简化了的罗马柱支撑着门面,一层的小卖部是当时全校唯一能买到糖果、汽水和学习用品的地方,二层是教工之家,三层左边是广播站、右边是校团委和武装部。小楼旁种着一棵棵大榕树和荔枝等果树,显得特别有文化、有情调。音专的林丽君同学推荐我到校广播站试试,我们的头儿是当时校党委宣传部宣传科长郭荣辉老师,我填了一张表,谈了几句后,他一抬头就说:“好吧,你明天就上广播站来报到。”广播站日常工作都是由学生在管理和运作,站长是中文系75级的李治莹,我知道他来自龙岩,一口带卷的普通话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同我一批来的中文系编辑黄宗平、王福贵,看样子都是身经百战,编审稿件时那个麻溜劲儿十分令人佩服。播音组的陈小红、陈阿敏据说原来都有列车播音员的经历。机管组当然就是物理系的老兄在把持。
广播站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有一个党支部,定期组织学习,在当时加入广播站的可是红舌,能将自己的声音传播全校的确是一种荣耀。物理系张之春副教授,长期在广播站与我们年轻学生一块儿值班,我的一些关于声学和音频的知识都是在认识他后了解的。当时广播站仓库里有许多老旧的中外音乐名曲大磁带,每到我值班时就让它们长时间飘荡在校园中,那年头已听惯了红歌齐唱的人,对这些所谓“靡靡之音、外国之声”却也心往神驰,我也是在这个时期了解了大师的许多作品。当时广播站有一台超美牌大型电子管收音机,具备收音、录音、播放等功能,硕大的动圈喇叭大、中、小组合有推背敲胸之效,保证了非常优质的音色返原,据说整个福建省只有师大这一台,是大跃进时期超英赶美上海最高尖端的产物。那年夏天我们在教工之家的会议室,策划了一场轰动校园的外国音乐欣赏会,大家精心准备了一些在当时禁止播放的乐曲,请了音乐专业的同学和老师做现场讲解。会议室、窗外和走廊全都挤满了人,场面令人感动,从大家的凝重神情中我看到了发自内心的渴望。据说后来有人告状,郭荣辉老师还专门召集我们开会,他淡淡地说:“放了就放了,播了就播了,下不为例”。大家缩缩脖子,又开始准备第二天的稿件了。
多年后,郭荣辉老师当了福建省教委主任,我问他当年的“告状”之事,他说“我兜着呢”。恩师啊,至今我还直呼他“老师”,从未称他的官衔。当时团委、学生会可以让学生参与的社团活动虽然不多,但都有老师引领、学生主持参与,影响并培养了一批敢于实践的“活动积极分子”。
艺术系的大艺术生活
1979年夏天,师大成立了以艺术系音乐专业学生为主的艺术团,团长是刘以光副主任,我们利用暑期到泉州、漳州、厦门巡回演出。78级黄镇同学指挥的双管制交响乐队演奏的罗西尼歌剧《威廉·退尔》序曲和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片断,严凤、片意欣同学漂亮的花腔女高音,黄明珠、陈华同学等人的新疆舞蹈《葡萄架下》等都是优秀的节目。我是艺术团唯一一个美术专业的参与者,友情出演独幕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和相声。当然,舞美景片都是美术专业78级班长王耀伟领着庄南燕几个哥们整出来的,77级的李晓伟在漳州还画了一批海报大肆张贴。高水平的演出,在三地引起了极大反响,场场爆满,连连加演,对扩大提升福建师大艺术系在社会的影响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毋庸置疑,我们的77、78级学弟、学妹们的确是精英干才。他们整体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养经常成为激起我们“妒嫉”之心和暗地里“竞争”的动力。当时的教学真是因才设课、因人施教,实践的机会很多,美术专业几乎每学期都到马尾造船厂、惠安鱼村、平潭岛、厦门东渡港等地体验生活、写生创作,我们油画组谢意佳、高一呼、林以友老师的许多佳作都是他们带队下乡和同学们一起写生创作的。系里各种专题的画展、各类型习唱习奏音乐会可以说每月都有,这样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方法,这种艺术多门类、多学科贯穿的人才培养模式,使76、77、78级学生发挥了他们长期社会生活积淀的优势,个性特质得到极大张扬。那时期的艺术系,教师敬业、学生好学,歌声琴声夜半不断,以至于美术专业学生难以忍受,常常抛以颜料瓶以表抗议。那时系里没有专职的辅导员,行政人员更少,73级高材生翁振新留校后就担任了我们的辅导员。大家服他是从他每天晚上在宿舍表演速写开始的,专业的优势很快就获得我们的欢心和尊敬。一年后他到浙美进修,回来后就忙他的专业,放手我们啦,基本由学生自我管理,一点小矛盾一个大人式的握手,好解决。
那年的母校、同窗的岁月,一生的挚友。